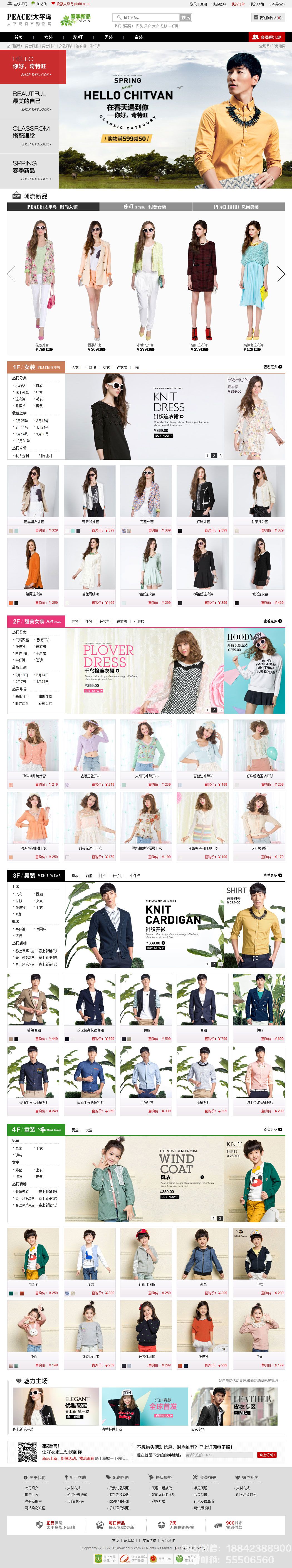天博康德诞辰300周年|保罗·盖耶:我是如何被康德哲学吸引的
发表时间:2024-04-22 10:24:24
文章作者:ezajj
浏览次数:
天博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为世界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说,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他,后来的哲学又从他这里流出。我国著名的康德学者郑昕也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时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义可以看作是应对当今时代平庸化的一剂良药。在2024年——康德诞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闻同中国康德学会共同策划,将陆续发布对世界各地资深康德学者的深度访谈,再次挖掘这位哲学家的光辉精神以及对于现今世界的意义。
盖耶教授编订的六本关于康德哲学的论文集当中,有三本属于“剑桥指南”系列(Cambridge Companion)。他在1986至2016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与艾伦·伍德(Allen Wood)共同担任剑桥康德英译本(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Kant)的主编,也是其中《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笔记和片断》这三本的主要译者。除了康德哲学,盖耶教授在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其美学部分)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三卷本《现代美学史》(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2014)和《哲学家带你看建筑》(A Philosopher Looks at Architecture,2021)的作者。
吕超:您是在哈佛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的。我们很想知道您最初是如何被康德哲学吸引的,大学里的哪些课程对您产生了影响,或者说您在中学时代已经开始阅读康德了?
保罗·盖耶:在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前的最后一年是第12年级。而在我读11年级时,在一堂英语课(也就是每个人都要上的语言和文学课)上,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份作业:找到一本你感兴趣的文集,阅读并撰写一份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做一次口头展示(oral presentation)。我们大致有两个星期准备这项作业。我那时住在纽约市郊的长岛。某个周末我到了市里,乘火车回家前在车站书店里看到一本平装书,那就是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很便宜,只有45美分,相当于现在的5美元或10美元。我买了这本书并在火车上开始阅读,读完时觉得它非常令人惊叹,尽管它的结论中有一些疯狂的东西(亦即我们对因果性的信念并不是合理的),它的论证看起来却很棒,而这一点非常令人迷惑。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读书报告,在课堂上做完口头展示后,每个人(包括老师)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却认为这很棒,是这一经历真正让我对哲学发生了兴趣。
随后的暑假我参加了为期六周的哲学课,这门课快速地介绍了各种哲流,一个星期是关于分析哲学的,一个星期是关于存在主义的,我们甚至可能还上了一个星期关于中国哲学的课。当我进入哈佛学院读本科时,我想要学习更多的哲学。实际上,那时我还在考虑成为一名建筑师,但在入学的第一年我拥有了如此出色的哲学老师,以至于之后我就坚持做哲学了。我在本科之前就读过一些康德,但读得不多,我确实读过叔本华,叔本华有一些基于康德思想的关于因果性的观点,他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对休谟做出回应。当我进入哈佛学院时,我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对康德发生了兴趣。本科第一年我们上了一门整整延续一年的人文学大课,这门大课是由两名哲学系的老师讲授,其中一人从前苏格拉底哲学讲到圣奥古斯丁,另一人则讲授了现代哲学和更一般意义的现代思想。我在这门课中读到的一篇文本是《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康德在那里对自由意志问题给出了他的解答。这门课有400多名学生,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由高年级研究生带领我们这些本科生学习康德的道德哲学。
随后的第二年,诺齐克开了一门《纯粹理性批判》的课。自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刘易斯(C. I. Lewis, 他也有点儿是康德主义者)于1955年退休后,哈佛已经有十二年没人开设《纯粹理性批判》的课了。刘易斯训练了许多出色的康德学者,例如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但他退休后,没有做同样工作的人接替他的位置。诺齐克当时还是一位助理教授,他之前没有研究过康德,也不是哲学史专家。但诺齐克声称,对他来说现在是时候研究一下《纯粹理性批判》了,而还有比开设一门课程更好的研究方法吗?诺齐克不需要成为一位康德专家,他是我遇见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是我遇见的最快的阅读者和最快的学习者。诺齐克显然在之前的夏天,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通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当时已有的评注。那是1967年的春季,而这意味着前一年(即1966年)施特劳森的《感观之缚》和贝奈特的《康德的分析论》已经出版了。这两本书使康德在分析哲学看来变得有趣,而诺齐克也读了这两本书,在那个时刻进入康德哲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诺齐克课上的一些学生正在攻读第一学位,一些学生则在做博士研究。诺齐克再也没有教过这门课,他并没有成为康德专家,我或许是那门课上唯一成为康德专家的人。我发现康德的某些观点有趣而可信,另一些观点则非常疯狂,比如先验唯心论。《纯粹理性批判》这部文本本身在我看来既迷人又充满挑战性,我在搞懂它之前都不愿意放下它。其他学生继续做其他事了,我则坚持研究康德。
在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第一年(即1969到1970年),罗尔斯开设了道德哲学的课程。他并没有讲授《正义论》,这本专著在之后的一年才出版。在《正义论》印刷之前,他分发给了我们一些其中的章节,但他实际上是用哲学史材料来授课的。罗尔斯在道德哲学课程中讲授了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或许我们还读到了密尔。罗尔斯在政治哲学课程上讲授了霍布斯、洛克、马克思,或许他并没有把康德包括进来。但无论如何,罗尔斯都讲授了康德伦理学。我开始对康德伦理学产生了兴趣,而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在这上面做太多功课。当《正义论》在下一年出版时,位于全书中心的章节被称为“康德式的解释”(Kantian Interpretation)。罗尔斯用康德式的术语来解释自己的工作,而这使很多人转向了康德伦理学。罗尔斯当时已经有很多学生围绕康德伦理学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工作了,这些学生大概比我年长六到七岁。在1960年代晚期,是施特劳森和贝奈特使康德的理论哲学变得激动人心并且与当时的哲学思考具有相关性,而在1970年代初期,则是罗尔斯使康德的道德哲学变得激动人心并且与当时的哲学思考具有相关性。
之后你可能会问我是如何开始研究康德美学的,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我在第一本书中以及之后一直在写作的主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部分。首先,在我准备写博士论文时还没有真正研究过康德美学,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深入研究过康德哲学中的这一部分。其次,我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主要靠做广告艺术和设计为生,但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画家。每次我回家度假时,父亲都会立即把我拖到工作室,向我展示他最近的作品,并问我感觉怎么样。我那时想的是:“我喜欢这幅画,不太喜欢那幅画。”但当是你的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会想要谈点更为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想:“或许从美学中我能找到一些可用的原则。”当然,你从美学史里学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原则。你无法以在数学中找到规则的方式那样,在美学中找到允许你对特殊对象做出判断的规则。当然,关于艺术之于人类生活具有价值的不同方式,你可以得到更一般的观念。一旦你拥有了这些一般的观念,你便可以开始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谈论个别的艺术作品了。但你找不到任何“规则”,你无法“证明”你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然而无论如何,我父亲是个思想开明的人。
吕超:您是剑桥版康德全集英译本的主编之一。我们很好奇如此庞大的工程是如何成功地完成的。比如不同的译者会对术语有自己的偏好和各自不同的翻译方式,您作为主编是如何协调所有这些译者的?
保罗·盖耶:艾伦·伍德(Allen Wood)和我的确尝试着制订某种形式的指导规范。艾伦和我制作了一张主要术语表,并将它发放给所有译者,同时艾伦和我也将自己作为译者来看待。我自己坚持如下的翻译原则,亦即译本的读者应当和原始文本的读者拥有一样多的、最好是同样的解释工作。如果某种东西在德语中是隐晦的和复杂的,那么它在译文中应当依旧是隐晦的和复杂的。如果某种东西在德语中是清晰的和不含混的,那么它在译文中应当依旧是清晰的和不含混的。否则的话,假若翻译将原文中隐晦的东西变得清晰,它就会向读者关闭解释的可能性,译者就是将自己的解释强加在作品上。当然,译者不可避免地总在把解释强加在作品上,但他需要试着有意识地去克制。译者应当尽量让句子保持原样,当原文中句子很长时,译文也应当保持长句。当原文中句子很短时,译文也应该保持短句。
当翻译《纯粹理性批判》时,艾伦和我首先做了第一份草稿,然后修剪,订正彼此的工作,等等。我有时会回头看看坎普·斯密的译本,用他的翻译来热身。我发现斯密不仅把某些长句截成了短句,有时还会把短句拼成长句,因为斯密在英国长大时养成了某种我称之为爱德华风格(Edwardian style)的写作方式,他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让康德听起来更像一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作家。但我们不应当那样做。我们发展出了一套指导规范,并试图让每一个译者都牢牢记住它。
对于挑选译者我们很有信心。大部分管理工作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挑选好的人来完成所有较低层面的工作。有时候这会涉及到协商,译者或许不喜欢我们的建议,我们就会与其争辩清楚,有时译者会说服我们,有时我们会说服他们。我们或许会完全不喜欢译者的工作,把稿子退给他们,要求他们思考如何修改。我们并没有强加文体上的统一,尽管剑桥设计了这种类型的东西。假若我们能够重做整套剑桥康德英译本,它或许能比现在更加统一化,但它已经花了我们太长时间,而我们都太老了。
这件工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真正在寻找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来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判断力批判》最早在由两位英国哲学家进行翻译,其中一人去世后我才加入了工作。任何一项延续了那么长时间的工程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一些人去世了,一些人陷入了争执,一些人则退出了。进程中总会存在某些调整,这有时会涉及到加入新人。至于《纯粹理性批判》,除了我们自己,艾伦和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把这本著作留给了自己来翻译。至于翻译之后的修订工作,我会做好某一部分的第一份草稿,把它交给艾伦。我们两人当时都有其他工作要做,都在写自己的书。当艾伦抽出时间时,他就会对我的翻译提出各种建议,再把草稿返还给我,然后我继续在上面工作,反之亦然。《纯粹理性批判》译本的成功在于我们两人拥有不同的技巧。在选择精确的词汇(即“措辞”[diction])上,我认为艾伦远比我要出色,当他建议用这个词时,他几乎总是对的。而当涉及“句法”(syntax)时——亦即在英语里找到可读的方法来保存康德的长句,使句子听起来非常像康德本人写的,但在英语中又是可读的——我则比艾伦出色。我和艾伦是互补的,我通常更喜欢他的选词,而他通常更喜欢我的句法。
剑桥康德全集要求翻译全都是新的,而不直接使用过去的译本。这部分地出于版权的原因。当然,玛丽·葛瑞格(Mary Gregor)已经为剑桥先前出版的单行本做了一些翻译,她按照我们的指导规范和艾伦的建议做了一些修订,但在《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这一卷完成之前她就去世了,艾伦最终完成了这一卷的翻译,所以他可能做了一些修改,但玛丽·葛瑞格本人却无法对此做出回应了。然而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的译本都是全新的。我们回到康德的原始文本,尽量少地依赖先前的英译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困难的。如果你研究康德很长时间了,那么斯密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本将印在你的脑袋里,你甚至能够听到它。而我们试图在脑袋里把它放到一边,回到康德的原始文本并重新翻译。康德有很多著作——包括他的一些科学著作和小论文——之前并没有英译本,而另一些著作的译本则有些老了。我们尽可能多地从头开始翻译,有时碰到非常困难的段落时也会查询其他译本。对于《纯粹理性批判》而言,我们不仅会查询斯密的译本,也会查询所有英译本,有时是麦克勒约翰(Meiklejohn)的1855年译本,或者缪勒(Müller)的1881年译本,甚至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英译本,即海伍德(Haywood)的1838年译本。有时我们会发现这些译者比斯密更为出色地解决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吕超:您的著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在中国也非常受欢迎。但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您对康德的解读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有时您似乎把康德的思想描绘成碎片式的,甚至是自己和自己相矛盾的。同时您使用了大量未出版的笔记,有时还会直接批评康德。某些读者可能会更偏爱艾利森(Allison)或其他学者所采取的为康德进行辩护的立场,很多初学者或许会对您的进路感到一些不安。但非常有趣的是,随着读者深入了解您的工作,他们会对您的著作产生更多的同情和喜爱。
保罗·盖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猜测部分的原因在于我确实想成为一名哲学家,我并不仅仅试图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从未想听起来不客气,但我并不致力于使康德在学生们眼里变得清晰。我从一开始就想要发现:康德思想中有什么在哲学上是可信的,有什么在哲学上是不那么可信的。我并不想说:这些是我们今天在哲学中所相信的东西,这些是康德哲学中与之相容的东西,那些是与之不相容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康德对什么观点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对什么观点的论证不那么令人信服,诸如此类。我想做的是内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我想要考察康德的论证,找出他的论证中哪里出现了缺口,哪里存在着假设,哪里论证得好。
有些做哲学史的人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历史学家,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研究的作者必须对于当代哲学是有趣的。相反,这些作者仅仅作为过去的片段而是有趣的。我并没有反对这些做哲学史的学者的进路,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严肃地把康德当作一位哲学家来看待,考察康德的论证在哪里是令人信服的,在哪里并不令人信服。我认为康德是一个十分实验性的哲学家,他持续不断地尝试着不同的论证,他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康德并不像休谟那样是一个早熟的哲学家(休谟在25岁时就想清楚了所有东西)。相反天博,康德花了很长时间来发展出他想要达到的结论,他试验着通达该结论的最佳方法。康德尝试了许多不同的论证,而这些论证并不总是整齐地嵌入一个单一结构内,有时这些论证甚至会彼此处于一种张力之中。康德的结论能够嵌入一幅融贯的图画之中,但他的论证却不能。
这就是我自己阅读康德的方式,我的体验说服了我采取这种方式,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它。然而,如果你看看《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经验的类比的第二个类比的文本,亦即康德关于因果性原理的证明,你就会发现在不同学者的计算中,康德论证因果性原理的次数也是不同的,比如坎普·斯密计算出了六次。康德甚至在出版的作品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论证着同一条结论,而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即使在出版作品中,康德也没有确切地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建构他的论证,所以他才不断尝试不同的东西。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康德对观念论的反驳,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才加入了这部分文本。康德很可能在修订进程中比较迟的阶段才加入了这部分文本。而在1788到1790年间,他又草拟了十二稿对唯心论的驳斥,这些文本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很显然,康德对自己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的论证并不完全满意,他依旧在试验着建构论证的最佳方式。在我看来,这正是康德的工作方式,那种关于他的每一步是如何嵌合在一起的、清晰的和单一的论证视野,从历史角度来看恰恰是不准确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反倒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
吕超:记得我多年前刚开始阅读康德哲学时,就参考了您的大作《康德与审美的主张》(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现在距离这本书的出版(1979年)已经过去40年了,请问您认为在康德研究领域哪些要素或多或少还保持着和过去一样,而哪些要素则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保罗·盖耶:这四十年来未曾改变的是康德本人的文本。康德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他的绝大部分(包括生前未出版的)材料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为人们熟悉了,尽管近年来关于他讲座的更多手写稿被发现,而这是在所谓一手资料方面唯一的变化。
当我开始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即Harvard University的本科生部)学习康德时,那是1960年代的后半段,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只有很少的英语研究著作,比如刘易斯·怀特·贝克(Lewis White Beck)对《实践理性批判》的评注。贝克是美国人,而说起英国人的著作,你就必须提到帕通(Paton)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评注,还有坎普·斯密(Kemp Smith)1910年代末期关于康德理论哲学的比较老的注释,以及帕通在1930年代出版的《康德的经验的形而上学》(Kants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后来斯特劳森(Strawson)的《感观之缚》(The Bounds of Sense)和贝奈特(Bennett)的《康德的分析论》(Kants Analytic)突然问世了。我立即阅读了这两本著作,它们非常激动人心,它们以分析哲学的语言和特定预设来接近康德,尤其是在斯特劳森这里。这些预设实际上并不属于康德本人,但这却突然使几乎所有事情都变得可能了。之后在我的博士研究阶段,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了。康德在这本著作里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康德也在罗尔斯讲授的课程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罗尔斯在他的道德哲学课程中讲授了康德,他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建构出自己的哲学。出于某些原因,罗尔斯没有太关注康德的政治哲学。那时很多人(主要在美国,但英国也有)开始对康德产生了热情。康德突然在他自己的历史中比在分析哲学对他的叙述中变得更为重要了。
我从博士论文关于《判断力批判》(特别是康德美学)的工作开始研究康德,而这样做是出于若干原因。我本身就对美学感兴趣,而且英语和德语学界那时并没有多少关于《判断力批判》的研究天博。因此这是一片开阔的领域,我可以直接对康德的文本进行思考和写作,而不必过多担心其他人说过什么。在我完成博士论文并在几年后将它重写为一本书的这段时间里,唐纳德·克劳福德(Donald Crawfold)的《康德的美学理论》(Kants Aesthetic Theory,1974)出版了,并且引发了细致的讨论。在我1979年出版的《康德与审美的主张》中,我的某些修订(这些修订并未出现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就是在回应克劳福德所提出的问题。
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阶段的最后一年,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第一次成为哈佛的访问学者。他带来了德语学术界的传统,将我置于这些传统面前。特别地在康德这里,这意味着全方位地使用康德的材料,包括使用康德的遗作(Nachlass),亦即在他手稿中那些他生前无意出版、但此后却被誊写并长年累月印制出来的笔记,包括使用康德讲座的手写稿,这些是由在他课上的学生,或者甚至可能是由专职记录员记录的。所以,这就是说不仅利用康德的出版著作,并且也利用所有的材料来试图对康德究竟在尝试着做什么获得一种更充分的理解。我向亨利希学习,而如果我的记忆是准确的话,卡尔·阿默瑞卡(Karl Ameriks)(他当时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德国学习了一段时间,他也开始使用上面提到的那些材料。我从《康德与审美的主张》开始的著作,以及卡尔几年后从《康德的心灵理论》(Kants Theory of Mind)开始的著作,都抬高了康德研究在美国的门槛。从那时开始你必须使用所有的材料。此外,我在博士论文中所做的一件事(尽管我并没有将它放入第一本出版著作中)就是深入康德美学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它的英国背景和德国背景。我一方面讨论了哈奇逊(Hutcheson)和伯克(Burke)等人,另一方面讨论了鲍姆嘉通(Baumgarten)、迈耶(Meier)、门德尔松(Mendelssohn)等人。大部分关于这个主题的英语研究都没有真正使用这些材料,而当时的德语研究则更多地用到了它们。这抬高了在语境(Context)中研究康德的门槛。尽管听起来这有点不谦虚,但我认为我和卡尔·阿默瑞卡改变了美国(或许也包括其他地方)对康德研究的期待值。
你或许会说,康德的出版著作当然应当享有相较于其他材料的优先地位,因为这毕竟是康德自己选择出版的,而其他材料只是一些草稿和实验,或许最终康德将它们放到了一边,而它们仅仅是偶然地幸存了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正确的。但我想要说,我们从这些幸存的材料中获悉了康德的工作方式。他持续不断地勾勒出论证的轮廓,他持续不断地尝试着抵达同一结论的不同方式,而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康德感到了现实地出版一本著作的压力时,他就将这些材料放到一块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出版著作中的论证必然优于其它他曾经尝试过的论证。这并不是什么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拼凑物理论”(patchwork theory)。那种“拼凑物理论”说的是,康德字面意思地将所有手稿放在一起,剪裁、粘贴、将其交给别人做成一份稿子,再送给印刷商。我说的可不是这个,而是康德持续不断地尝试着什么才是通达他想要得到的结论的最佳路径。你不能自动地假设他在某本书中安置的一个特定版本就是事实上最佳版本的论证。有时在他笔记中出现的某些版本的论证里,我们发现了其他更有趣的路径。
当然,这对康德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构成了挑战。现在,你必须处理远比我们当年起步时更多的材料,除此之外还有四十年间积累起来的研究文献。英语和德语是康德研究使用的主要语言,意大利语作品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但英语和德语仍然是主要语言。在世界各个地方——特别是就我熟悉的美国、英国、德国而言——人们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越来越早地出版自己的作品。研究文献不是以算数的方式,而是以指数的方式在增长。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年轻学者面临着比我们那一代人更大的挑战。《康德研究》(Kant-Studien)每年都会出版一份过去一年里关于康德哲学的文章和著作清单,而每一年都有数千的条目出现。没有人能在一年之内将这些文献全部读完。因此人们需要挑选,而这又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阅读最好的期刊,它们是Kant-Studien,Kantian Review,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等等。关注这些期刊,发现令你感兴趣的东西。另一种方法则是相互交流,因为没人能够阅读所有的东西,但某些人可能读过这篇新文章,而某些人则可能读过那篇新文章。
然而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件事,我认为对于老文本的每一种严肃而具体的哲学解释,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与当前的哲学问题、当前的哲学话语、当下的哲学风尚联系在一起。无论作者是否想要这样做,这一点都是无可避免的。新的解释者们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根据当前的哲学术语和哲学主题来解释已经被研究了数年甚至数世纪的同一部文本。由于哲学术语和主题在不可避免地变化着,解释者总会有一些新的工作可以做。如果你看一下近期康德研究文献里出现的认识论中的概念论(conceptualism)与非-概念论(non-conceptualism)之争,关于康德是不是道德实在论者(moral realist)的争论,以及道德实在论与建构论(constructivism)之争,(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在新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层面进行的争论。你会发现当年轻学者讨论康德和其他作者时,他们会使用不同于50年前的康德研究中的概念。因为一般的哲学形势(philosophical landscape)改变了,所以人们解释文本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对某种形式的观念论的特殊运用不可否认地是真的,亦即你总是从自己在地上的视角来观看世界。你能够调整你的视角,但你永远无法全然脱离人类的视角而直接抵达客体。这一点对于哲学研究也是真的,它总是从某个视角出发写成的,这个视角或是突然地、或是没那么突然地随着时间而改变,由此解释本身也将随着时间而改变。
我认为自己十分地幸运,人们在《康德与审美的主张》出版40年后,在《康德与知识的主张》(1989年)问世30年后还在阅读这两本书。对于解释性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一种很长的寿命了。这或许部分地缘于我有意识地并不将过多的当代哲学带入进来,而试图用康德自己的术语来思考。但这并不等于接受康德的所有论证。我将诸如一贯性(coherence)、合理性(soundness)等基本标准用于讨论康德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并不回避引入一些其他的哲学假设。然而,我尝试着并不简单地将康德翻译成当代哲学术语,因为那或许在十年之内在人们看来还是有趣的,但随后事情将会已经向前发展了。
吕超:我们现在可能会感到用英语写成的康德论文和著作甚至比用康德的母语写成的作品更有影响力。在您看来造成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除了罗尔斯的贡献之外,其他改变康德研究形势的因素还有哪些?
保罗·盖耶:这里有不同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完全不限于哲学学科内部,那就是英语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这部分地与大英帝国的地理疆域有关,部分地与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位置有关。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学习英语,或是作为他们的母语,或是作为第二语言。当然对于这条规则是存在例外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人们都在学习英语,因此很容易把英语作为科学交流的语言,就如曾经的拉丁语和19世纪的法语一样。
而第二点因素我认为是德国哲学的风尚。在过去四十年间,当康德在许多英美学生和学者眼里变得越来越有趣的时候,德国却越来越专注于当代哲学和分析哲学。和过去相比,真正研究康德和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人在德国变少了。德国人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毕竟这些文本是用德语写成的,他们能够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好地理解文本,即使后者已经做了很多年研究。但如果你看一下德国大学在过去四十年间的教授任命,大多数教授席位都给了做某些版本的分析哲学的人。这就是风尚的变化。近期在美国做一个优秀的康德学者,比在德国本土要更具声望一些。
你还谈到了罗尔斯的杰出贡献,这一贡献不仅在于他自己的著作,也在于他培养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学生。在罗尔斯事业发展中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在他1960年代刚刚来到哈佛时就有很多学生:小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 Jr),奥诺拉·欧奈尔(Onora ONeill)、克里斯汀·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安德鲁斯·瑞斯(Andrews Reath)、安德鲁·派普(Andrew Piper)(他至少在美国也是很著名的艺术家)等等。罗尔斯训练了这些学生,但“训练”(train)并不是一个确切的词,因为罗尔斯并不制造门徒,而是启发学生,然后后者就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工作,从而在英美两地使得关于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变得生机勃勃,并且创造出了康德式的伦理学(Kantian ethics),亦即被康德启发、但并不属于对康德的解释的这样一种伦理学。许多人认为道德哲学有两种基本范式,一种是康德式的伦理学,另一种则是功利主义或者后果主义的伦理学,而由亚里士多德启发的美德伦理学则有点缓慢地跟在后面。但康德主义成为道德哲学的一种基本范式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极大地归功于罗尔斯。康德哲学的其他部分,例如认识论,或许在美国就不是范式性的。然而也有很多人研究康德的科学哲学,例如米歇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而我则在研究康德美学。现在一些学者也对康德的政治哲学感兴趣,因此对康德哲学中其他部分的研究也是生机勃勃的。
吕超:随着二手文献的急速增长以及康德哲学中各大领域已经得到探索,年轻学者做出新成绩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在您看来,康德哲学中还有哪些问题并未经过充分讨论、但却值得年轻学者进一步探索呢?
保罗·盖耶:我刚才说过,年轻学者将带着不同于老一代学者的背景来接近文本。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提出在他们自己看来有趣的问题。同时,他们不应该自动地假设每一个变得流行的问题都真的值得被提出。年轻学者不应当仅仅关注最新的期刊文章和三年内出版的专著,而应当回过头去看看一些经典解释,比如贝克、阿默瑞卡、我、或许还有帕通等人的作品,然后他们或许会发现这些老一代学者已经提出了某些有趣的问题,所以他们可以告诉自己:不要被当代的问题转移了注意力。
至于康德哲学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领域,我想说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特别是关于康德政治哲学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比如我正在完成一本关于康德和门德尔松的书。我考察的是他们之间贯穿两人整个事业阶段的学术关系。你或许会认为很多学者已经写过这样的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找到了一篇写于1929年的试图讨论康德和门德尔松学术关系的德语文章,然而从那之后,就没有人再写过关于该问题的专著了,这有些令人吃惊。此外,学界关于康德从鲍姆嘉通那里学到了什么、拒斥了什么的问题也没有很好的研究。的确有一些研究康德和休谟、康德和哈奇逊的关系的,但这还不够。而学界关于康德和沙夫茨伯里(Shaftsbury)的关系也没有足够的研究。同时,关于康德的接受史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这是我最近在干的另一件事。有些学者——特别是在德国和说德语的地区(如瑞士、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在研究莱茵霍尔德(Reinhold)、迈蒙(Maimon)、和舒茨(Schulz)等第一代读者对康德的接受,而英语著作中这方面的研究则很少。就我所知,以上提到的迈蒙等人的著作几乎没有被翻译为德语之外的语言。此外,我发现昨天韩水法教授关于康德与人工智能的开场演讲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因此在康德与当代科学、当代文化的发展的关系上也有很多研究可以展开。
吕超:您在独立的美学领域也有非常杰出的贡献,比如那套关于现代美学的三卷本专著。我的问题是,当我们谈及二战之后的当代艺术(通常是后现代艺术)时,很多当代艺术作品似乎并不是优美的,反倒是丑陋的,它们无意于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而是仅仅想宣扬某种理念。请问这些作品可以被归于审美的一般范畴之下吗?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当代艺术的观点,包括它们的潜在优势和问题又在哪里。
保罗·盖耶:首先让我谈一点关于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的观念,然后再谈谈当代艺术。我不是艺术史学家或者艺术批评家,而将美学家的工作和这些人的工作区分开是很重要的。美学这个术语是由鲍姆嘉通在1735年作为和逻辑学并行的概念而创造出来的。美学和与理智活动(intellection)相对立的感观知觉(sensory perception)相关。鲍姆嘉通意欲让美学成为一门关于感观知觉的科学,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解释关于感观知觉的一般性科学到底是什么。鲍姆嘉通专注于对艺术的知觉,但确切地说“知觉”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因为鲍姆嘉通脑袋里首先想到的是诗歌,而不是视觉艺术。然而,他并没有把艺术的这些有趣属性限定在美上面,而同时也讨论了崇高。当然,他并没有用“崇高”(sublime)这个概念,而是将崇高称为“感性的量”(aesthetic magnitude)。康德从鲍姆嘉通那里学到了这个术语,但并非之后的每个人都直接使用这个术语。康德讨论了自然和艺术中的美与崇高。崇高首先存在于自然中,因为康德并不认为艺术强有力到能够产生出崇高感,但自然既可以产生出对崇高的体验,也可以产生出对美的体验。
美学中的重大转折发生在黑格尔那里。在美学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想要论证说自然是没有趣味的,因为它不是从精神诞生出来的精神,它不是人类的或者精神性的创造物。至于这里的精神究竟意味着人类精神还是更高的东西,在黑格尔研究者那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黑格尔本质上说放弃了自然美,或者说把自然的属性从美学中排除了出去。因此通过这一排除,美学从黑格尔开始也就开始意味着艺术哲学。这并不必然地指哲学内部一种特别的理论,而仅仅是“艺术哲学”这门学科的名字。一些身处哲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的人(比如文学系的人)将美学等同于关于美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等同于“艺术应当追求美”这一命题,由此他们得以谈论“艺术的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 of art)(这种表达在哲学家听起来却是冗余的)。任何艺术理论都是美学的一部分,但当这些人谈论艺术的美学理论时,他们声称艺术应当或者必须以美为目标,因此他们会认为二战之后、甚至基本上始于杜尚(Duchamp)的二十世纪艺术都拒斥了美学、摧毁了美学,诸如此类。但在哲学家听来,这些论断毫无意义。艺术无法拒斥艺术理论或者艺术哲学,艺术只能反对某种特殊的艺术理论,而不是反对关于艺术的哲学言说这件事务本身。
因此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二战之后诸艺术领域内的发展——尤其在视觉艺术中,但也有一些音乐运动(如约翰·凯芝[John Cage]的作品)和一些文学运动——它们或许摧毁了“艺术应当追求美”这一观念,但并没有摧毁哲学美学(philosophical aesthetics)的实践。如果你看一下美国1960年代以来哲学美学的发展——从阿瑟·丹托(Arthur Danto)1964年关于“艺术世界”(Artworld)的著名文章开始,也包括乔治·狄肯(George Dickie)在196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你会发现哲学美学这一学科(或者说次级学科)试图建构出一种艺术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适用于那种不再对美、而对其他东西感兴趣的新型艺术。如果向前回溯一个世纪,我们还会发现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的著作,这本著作的英译名是《丑的美学》(Aesthetics of Ugliness)。按照某种解释,这个标题就是一种自相矛盾,因为美学仅仅关系到美。但罗森克兰茨的意思是,这本书是一种展现丑的艺术理论,或者关于艺术为什么必须既包括美,也包括丑的理论。在美国,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二、三十年间,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首要主题就是对艺术的定义,而不是对美的定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很多艺术是丑的,是和美不相关的,甚至是敌对于美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更为一般的对艺术的定义,从而囊括针对当代艺术的美学工作。
你也问到了我个人对当代艺术的看法。西奥多·阿多诺声称奥斯维辛之后不可以再有诗歌,因为人类历史中发生了如此可怖的事,诗歌创作,或者更一般地说,对美的对象的生产这件事本身都是粗俗的。相反,我们应当表达人类历史中可怖的一面,因此艺术应当专注于丑,而不是专注于美,因为丑才表达了人类真正是什么样子,以及人类历史变成了什么样子,诸如此类。这种“艺术应当专注于人类处境中的丑,而不是美”的情绪传播得相当广泛,即便人们并不知道阿多诺的作品,或者他们并没有在引用阿多诺的原话。总之,这种传播得相当广泛的情绪是:人类处境是丑陋的,而我们应当致力于去表达真相。
然而,也有思考事情的其他方式。你可以说人类能够做出、并且已经对彼此做出了可怖的事,人类生活的许多事实的确是丑陋的,因此我们在生活中比以往更需要美,难道不是这样吗?在2000年左右和在此之后,至少一些人开始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了。人类生活中有许多丑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它们、理解它们、改善它们。这件事很重要。而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将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意味着通过创造美的艺术来帮助人们。所以我并不同意阿多诺的以下观点,即奥斯维辛之后不应当再有诗歌,如果这个观点意味着奥斯维辛之后不应当存在美的话。我同意“永不遗忘”的理念。我们不能假装例如奥斯维辛之类的一切可怖事件从未发生,也许艺术所扮演的某种角色就是保持对这些可怖事件的鲜活记忆,向未曾在那里经历过这一切的下一代人表现和传达这种可怖,因为艺术能够强有力地传达信息,至少有时候能够比枯燥的历史书和一捆数据更为有力地传达信息。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坐在一堆灰烬上,仅仅回顾着这些可怖的东西而不在生活中继续前进。美的经验对人们非常重要。看看这儿,看看四周(指北大人文学院)。人们维护着这些美丽的建筑,种植树木,照料花园和篱笆,因为美对人类非常重要。所以在我看来,坚持认为艺术不再以美为目标——这种观点既是缺乏动机的,也是不正当的。或许并非每一种东西都应该被艺术当作合法的目标,并非每一件单独的艺术品都应当以美为目标,但就我所理解的艺术来说,美的确是艺术的一个合法目标,除非人类种族出于对过去或当前之事的绝望而仅仅希望毁灭自身。我们的生活中需要美,自然能够提供美,自然尤其在这方面能够帮到人类,而当自然没有帮到我们时,艺术又能够提供美。
现在我特别地来谈谈一些各种艺术领域。我可能因为说这些话而陷入麻烦,因为我的姐姐是一位视觉艺术画家(笑)。我认为绘画活动在很多地方有些迷路了。阿瑟·丹托曾经论证说(而且很多人也承认这一点)绘画是一种表象的活动(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所以一旦摄影术被发明出来并得到完善,绘画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有一段时间人们尝试着用绘画去做一些别的事,由此我们有了非-表象性的(non-representational)绘画,比如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或者更一般意义的非-具象性的(non-figurative)绘画,就像始于俄国画家维支(Malevich)的至上主义(Suprematism)。我觉得从1980年代起,虽然一些著名的画家依旧拥有绘画工具(如刷子、帆布、木头等东西),但他们并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现在依旧有人在绘制肖像画和风景画,但他们不再得到关注了。因此我认为先锋绘画已经迷路了。然而这并不证明……谁知道未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但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现在的小说家和以往一样多,甚至比以往更多。其中一些人在尝试做实验小说家,另一些人则干着小说家从十八世纪起就在做的事,也就是讲述虚构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捕捉到了关于人类生活之本质的深层真相,它们更为一般地或更为具体地描绘了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城市、特定的生活圈子、这一邻里或那一邻里的居民、这一社会处境或那一社会处境中的人,诸如此类。此外有人在写诗,有人在做音乐,当然还有人在做电影、摄影、舞蹈和其他艺术,它们中的许多在我看来并没有迷路。它们有时在寻求我们体验为美的东西,有时在寻求我们体验为惊悚的东西,有时在寻求我们体验为崇高的东西。它们具有不同的目标。然而这些作品看起来和过去很不一样。20世纪的小说读起来不同于19世纪的英国小说、18世纪的法国小说、或者是《源氏物语》。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看起来非常地不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很多角色,而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只有很少的几个角色和一支歌队(chorus)。戏剧的结构也是完全不同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推进得很快,仅仅描述了一天之内发生的事件,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则能够描绘在几天、甚至几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事件。然而这样的不同又有些肤浅,因为在一个更深的层次,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在做同样的事,他们都在捕捉关于他们各自世界的某些真相。希腊世界当然不同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因此捕捉这两个世界的艺术看起来也非常地不同。但两者又在做同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允许生活在其中一个时代的我们从内部去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类生活,去理解那些人是如何感受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或者允许生活在这两个时代之后的我们,对处于那些环境、那些时代的人类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之间的相同与差异获得一种理解和感受。